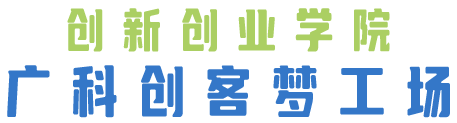
一、民兵营长的儿子
我出生那晚,爹将一把镰刀塞在我摇窝底下,这是民间的习俗——辟邪。
摇窝的被套是土改时分到的一块蓝印花布,被面上还留着周家地主小姐绣的半朵牡丹。
娘说我学会走路前就认得稻种——爹总把我搁在箩筐里,去开会时箩筐硌的我屁股生疼,我却能闻到他汗衫里晒干的稻谷香。
“当年公社大锅饭,谢营长舀粥永远只舀半勺,自家娃饿得吃糠咽菜。”村里老人咂着旱烟回忆。
我七岁就下田挣工分,全身沾满泥巴,看父亲在晒谷场上吆喝:“按劳分配,偷懒的扣三斤粮。”
10岁那年,我偷摘了生产队的菜瓜。爹把我吊在堂屋大门上。蔑条破空声响起,“咻咻咻”,一声接着一声。
我拼命挣扎,哭喊声撕裂整个屋场,蔑条抽裂了周老爷的“福寿”二字。
夜里娘用茶油给我抹背,油灯把爹的影子胀满整面墙:“饿死不能偷公家粮,这是规矩。”
我至今记得那晚月光如水,照着屋前那棵酸柑子树。
爹抽完鞭子后坐在门槛上抽烟,他用蔑条抽裂了旧时代的体面,却在我背上烙下新秩序的戒尺。
1980年春天,生产队正式宣布分田到户。
们家分到了五亩水田,还抽中了村东那头老水牛的五分之一股份。这头牛虽然年纪大了,但力气还在,五家人商量着轮流使用。
爹娘高兴得几夜没合眼,每天天不亮就带着全家人下地。
那会儿我刚满15岁,插秧打谷已是一把好手。公粮交完后,家里终于能存下些余粮,锅里的米饭渐渐稠了起来。
第二年,我们还分到了一片茶山。爹盘算着光种田不行,得找点副业。
他东拼西凑买了台碾米机,在村里开起榨油坊。农闲时我们就上山摘茶籽,回来加工成茶油换钱。
记得有次邻村有人来订了二十斤茶油,爹硬是拉着板车走了三十里路给人送去。回来时虽累得直不起腰,但脸上挂着笑。
"以后日子肯定越来越好。"那年我第一次看见爹抽烟时嘴角露出轻松的神情。
二十五岁的春天,公社组织露天放映电影《补锅》。银幕搭在村口的大槐树下,全村老少都搬着小板凳围坐在一起。
隔壁村的田桂英坐在我的前排。她扎着两条粗壮的麻花辫,鬓角因为出汗而黏住了一些碎发,在月光下泛着黑釉般的光泽。
银幕上刘大娘骂李小聪:“你补锅的还想讨我女儿?”桂芬噗嗤笑出声,麻花辫里泛着稻草香。
那夜我偷了爹的民兵哨,学电影里吹《采茶调》,吹得满嘴铁锈味。
“嫁汉嫁汉,穿衣吃饭”,桂英爹开口就要八担谷的彩礼。
我闷头扎进自家承包田,试种从县农机站讨来的“威优63”杂交稻,据说这种稻谷产量高、抗病性强。
浸种水温要卡在35度,比伺候月子还精细。”这是农机站老周的原话。
我在秧棚支起竹床,枕边摆着温度计,半夜常被露水打湿的衣裳冻醒。每次迷迷糊糊睁开眼,第一件事就是摸过温度计看看,生怕水温有丝毫差池。
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一个月,本以为熬过了育秧的难关,却没料到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。
4月的暴雨说来就来,一天午后,乌云压顶,狂风大作,暴雨倾盆而下,溪水很快涨到没腰深。
更大的难题是基础设施的匮乏。丘陵地区没有机耕路,也没有灌溉水渠,机械根本无法顺利运行。
于是,六户人家卷起裤腿,自己动手修路挖渠。
整个施工过程堪称与自然博弈的壮烈史诗。犬牙交错的沟壑与起伏不定的地势构成三维迷宫,每掘进一尺都要与板结的冻土展开角力。
白天干活时,大家的手上磨出了血泡,衣服被汗水浸透又在寒风中结冰,但没有人抱怨,更没有人退缩。
晚上回到住所,大家围坐在昏黄的灯光下商量第二天的工作计划,同时研究如何改进田块布局,让机械能够更高效地作业。
通过反复测量与规划,我们将零散的小块田拼接成适合机械作业的大块田,并修建了更多辅助道路,以便农机能顺利通行。
现在,我最开心的事就是回家喂鸡,因为远在深圳的小孙子再三叮嘱:“不买鸡蛋,只吃爷爷家的鸡下的蛋。”
说起小孙子,他的可爱模样总让我忍俊不禁。每次视频通话,他总是把脸贴到镜头上喊:
“爷爷,奶奶过来深圳了,你也过来呀……”听着他的声音,我的心里满是甜蜜和牵挂。
这代孩子活得拧巴——捧着进口奶粉长大,倒稀罕土灶灰里煨的红薯;
能背出二十种恐龙学名,却分不清秧苗和稗草。
编辑:校企合作与实习就业处暨创新创业学院 陈晓彤
审核:校企合作与实习就业处暨创新创业学院 姚圣梅

关注微信号
©版权所有:云博(中国)
广州校区:广州市广从九路1038号滨海校区:茂名市高地智慧城慧城三街8号
粤ICP备20000181号-1 网站技术支持:品牌运营中心